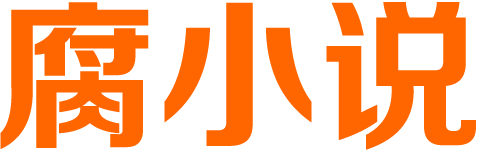西窗竹(58)
“你看不下去?我逼你亲自动手了吗?!”陆桓城情绪失控,死死掐着陆桓康的脖子嘶声咆哮,“他怀了孕,明天就要生下你的孩子,我骗你亲手剥了他的皮、抽了他的筋,丢进油锅里烹煮,等烹烂了再皮笑肉不笑地告诉你杀错了人,这才叫真正的残忍!如今我光明正大叫你看着他死,连刀都不逼你拿,你有什么脸面对我说看不下去?!”
说完扬手狠狠一掼,紧跟着一阵桌椅翻倒之声,陆桓康栽在墙角,身形狼狈,伸手捂住了涌血的唇鼻。
他垂着头,再也无颜开口求情一个字。
愤怒中爆发出来的一番话,扇的是陆桓康的脸,剜的是陆桓城的心。
这辈子他都忘不掉,亲手杀了晏琛的人,是他自己。
有那么一瞬间,狂热的复仇欲望冲昏了头脑,他是真的想用匕首抵住陆桓康的脖子,逼他亲自动手,剥下一张血淋淋的皮毛,把那狸子丢进油星四溅的锅里,眼睁睁看着它挣扎至死。一双手沾满情人的鲜血,一辈子活在肝肠寸断的痛苦里。
世间不该只有他一个人,孤独地承受着失去所爱的剧痛。
太不公平。
良久,陆桓城才从崩塌的情绪中缓过来。身体被抽空了最后一点力气,虚软地靠在墙上,目光飘浮,一片黯淡。
他竟变得这样嗜血而扭曲。
这一晚发生了太多变故,他痛失晏琛,与胞弟反目,亲缘、情缘一刀断尽,而种出了一切恶果的祸根,是那只心肠歹毒的狸妖。
收走它吧。
让恩怨了结在今天,不遗留到明天。
明天,他还要平静地过日子,还要完成晏琛的遗愿,好好养大他们的孩子。
陆桓城望向老道,倦乏的笑容里带着一丝难言的尴尬:“玄清道长,陆家的家务事……弄成这般模样,让您见笑了。我今天……实在是有些疲累,不想再深究此事,也不愿家中见血,烦请您带走这只狸子,替我施罚惩治。过段时日,待我处理完府内杂事,必会亲去鹤云观拜访,捐银酬谢。”
“镇邪收妖,本是我分内之事,亦能增加修为,陆当家不必太记恩情。”玄清道长淡然一笑,示意他无需挂心,“反倒是我道行浅薄,不能救回那株青竹,心有歉意。”
陆桓城闻言摇了摇头,凄楚笑道:“这是天意,哪里能责怪道长?百余年天地灵气才聚出一根灵竹,活生生的,能说会笑,可交到我手里不过半年,就弄得魂飞魄散。我这般薄情寡义,玷污了他的衷情,委实配不起他。上苍将他收走,也是我自作自受……怨不得他人。”
“如是,还望陆当家节哀。”
玄清暗叹世事无常,长吁了一声,而后振开衣袖,径直走到濒死的狸妖面前,从袖中取出一只青玉宝葫芦与一枚乾坤八卦镜,就要行收妖之事。
镜内射出一束如剑寒光,照在墙壁,晦暗之中几经折返,立刻吞噬了满厅黑暗,遍地尽是耀眼的明光。阿玄被那光线一碰,身躯猛颤,尖利地嚎叫起来。
陆桓康见状,脸色遽变,踉跄着扑到阿玄跟前,以身体牢牢护住,不肯相让半分,对陆桓城喊道:“哥,我这条命你也一并拿去吧!换他一个干干脆脆的死法,免受油锅烹炸之苦!这件事,我,我也有错的,煽风点火的是我,火上浇油的是我,猪油蒙了心非要弄死晏琛的人也是我,不能叫阿玄独担!我和他一起还命,总共十条,哥,总共十条,求你饶了他吧!”
“够了!”
陆桓城眼中落泪,一拳砸在桌案上:“你还嫌陆家死的人不够多吗?!”
正在这混乱的当口,内室传出了一阵细软啼哭。老管事抱着笋儿出来,说孩子没来由地突然惊哭,怎么也哄不住。
笋儿是陆桓城心尖上的宝贝,落一滴泪他都舍不得,慌忙接过襁褓,抱在怀中轻晃着安抚。偏生笋儿啼哭不止,卯足了劲儿越哭越急,一张小脸儿憋得通红,喘不过气似的,眼睛鼻子糊满了泪涕,险些活活哭晕过去。
陆桓城效仿老道,摘下一把嫩叶喂给他。可这回不顶用了,笋儿张嘴“噗噜”一吐,水露也不要,嫩叶也不要,小嗓门儿扯到比天高,不一会儿就哭哑了嗓子,干巴巴地呛咳。
陆桓城第一次做父亲,既生疏又易慌,几乎急疯,忙向玄清求助:“道长,他莫名哭成这样,究竟怎么回事?是不是被邪魅惊扰了?”
“有我在此处,邪魅不敢靠近。”
玄清思忖了一阵,收起手中的八卦法器,徐徐道:“方才孩子骤然啼哭,正是我欲收妖之时。初生婴儿,灵息最为洁净,恐怕见不得杀生。陆当家不妨将他抱去远处,一来可避过杀生,二来可避过这狸妖的怨气,以免今后被它纠缠。”
陆桓城会意,便把孩子抱出了前厅。
谁知刚走了几步,笋儿忽然一踢襁褓,猴子抹油似地翻了个身,两只小手拼命伸向门内,半截身子瞬间滑出了臂弯。幸亏陆桓城反应敏捷,半空及时托住肩膀,才没让这肉嘟嘟的小娃娃跌到地上!
“笋儿?”
陆桓城大惊,抬头与玄清道长对视了一眼,同时意识到状况有些不对。
笋儿不是怕杀生,他是不愿离开这儿。
出生才一天的孩子,连骨头都是软的,陆桓城哪敢强行制住他,只好顺着那小手扑抓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去。进屋、拐弯、越过桌椅、靠近屋角,越走越觉得诡谲,最后竟出人意料地停在了阿玄面前。
笋儿泪水涟涟,不安分地在父亲怀中扭动,想要挣脱襁褓,去靠近那只危险的狸子。
这简直是幼兔扑到虎口前,自寻死路!
陆桓城无论如何也不肯,笋儿便倔犟地狂哭不止。玄清道长在旁看着,白眉微皱,似是隐约想起了什么,示意陆桓城勿要担忧,暂且遵从笋儿的意思去做。
第五十一章 涉险
阿玄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,姿势有些畸形。
他的腹部绵软,随着呼吸一缩一抽,被长鞭抽烂的伤口狰狞而恐怖,粉鼻子滴滴答答淌着血,浸透了脸颊上黑白相间的绒毛。
一只靛蓝的襁褓被放到了跟前,距离极近,甚至碰到了他受伤的前爪。
襁褓里头躺着一个皱巴巴的小婴儿。
这群人都疯了,阿玄想,竟敢把孩子送到他面前公然挑衅,难道就那么笃定他身受重创,连这细细的小脖子也咬不断吗?
不,咬得断,只要他愿意。
阿玄冷冷地哼了一声,鼻尖不慎喷出一堆血沫,他有点尴尬,伸出舌头舔去了,才懒洋洋地打量起这个胆大包天的奶娃娃来。
仔细一瞧,倒是真的很像。
眉眼,唇形,鼻子,耳朵……哪儿都像极了那根傻兮兮的竹子。
唯独个子小了一点儿。
笋儿比他的狸身还要小,像一尊白瓷的招财童子。小胳膊与他的前爪一般粗细,手指短短的,豆苗似的十根,皮肤水嫩,透出几分单薄的血色,用带刺的舌头轻轻一舔,仿佛就能刮下一层皮肉。
分明这么脆弱,为什么偏偏三番五次也伤不了呢?
阿玄绞尽了脑汁,却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,总觉得有什么不一般的东西在阻碍他伤害这个孩子。
笋儿生了一双滴溜溜的、黑亮的大眼睛,像两枚小镜子,映出阿玄此刻狼狈不堪的样貌。他大大咧咧地笑着,鼻涕打出一串泡儿,唇角挂着流不完的涎水,黏乎乎,脏兮兮,表情因为懵懂而显得大胆无惧。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