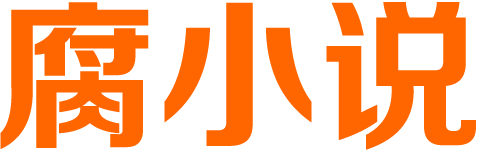西窗竹(46)
陆母又记起了什么,犹豫一会儿,试探着问:“你身边为祸的那个,那个晏琛……可除掉了?”
此话一出,陆桓城的动作立刻僵住,手指竟止不住剧烈发抖。眼中的水光刚淡去一些,又浓回了初时。他垂眸不语,呼吸久久难平,半天才哑声道:“他……不在府里了。”
不曾除掉,只是不在府里。
就算这样简单的六个字,陆桓城也说得万般艰难。
陆母听出了话中之意,但并未责怪。她是过来人,既享过饴蜜的情爱,也经历过肝肠寸断的丧夫之痛,如何不能体会陆桓城的心情?他眼下这伤情模样,分明还对那个少年惦念不舍——晏琛是长在心头的一颗瘤子,明知不能留,用钝刀割去了,仍会鲜血淋漓地疼。
她握着儿子的手,安抚道:“城儿,这件事……不是你的错,娘不会怪你。哪怕你现在还想着他,娘也理解。我们是肉体凡胎,不是铁打的,扛不住这样伤心的事。心里头受了伤,总要先疼一阵子,等过去十天半个月,慢慢结了痂,才会痊愈。城儿,你莫要勉强自己,慢慢地忘,慢慢地恢复,日子还是要一样过下去,明白么?”
陆桓城点了点头,哽咽道:“娘,我明白。”
雨丝纷缭,落下万道垂帘。陆桓城一开门,斜风夹着冷雨扑面而来,料峭的寒意冻僵了面孔。
他抬头望着阴郁的天色,神情哀凄而彷徨。
五天了。
晚春清早,连粉墙重重的府里都寒气逼人,十里之外的萧索山野,会冷成什么模样?他的阿琛一个人住着,无人陪伴,可还安好地活在这世上,也瞧见了这一场春雨?
想着便又狠狠自嘲起来,嘲笑自己捅不破心障,时至今日还心存痴想,不肯将晏琛当作妖精,不肯承认他是一株艳丽的、极毒的夹竹桃。
环翠见他要离开,递来一把伞。陆桓城起初没接,入雨走了几步,脚步顿住,不言不语地回来取走了伞。
晏琛已经不在了。
纵然大雨倾盆,也不会再有人撑着一柄油纸伞,伫立在藕花小苑的栅栏后头,盼他归家。
陆桓城出了佛堂小院,撑伞站在岔道口,茫然望向前方——这是他的家,他需要一张睡觉的床,可他无处可去。
脚步被什么牵引着,仍走了最熟悉的一条路。
小径曲折,探入丛丛新绿,盎然的绿意簇拥着一道短墙门洞。推开湿栅栏,往里走去几步,整座空荡的小苑安静异常,只剩下细密的雨声。远处房门紧闭,窗户灰暗,一片沉沉死寂,连灰尘也被泼天的雨水打湿,不肯飞扬起来。
陆桓城立在雨中,看着无数的水珠砸进莲池。
晚春无花,几片伞叶高高低低地撑出水面,须臾盛满了水珠,不堪重负,忽地翻弯了细茎,把雨水倾倒入池,又颤抖着直回来,左右摇曳不歇。
这人烟寂寥的陆宅啊,还是同样的三口人,还是重复的生活,分明和半年前一模一样,却也什么都不一样了。
只因晏琛曾来过。
鸳鸯喜帕,粉香纱帐,轩窗外一夜小雨,床帏内喘息缠绵……所有的回忆都在那一天晏琛离开之后,被紧锁的房门封存了起来。这间屋子是一座坟,里面葬着他死去的爱情。
坟外藕花盛开,坟里魂灭心冷。
甚至整座藕花小苑,都埋葬着他充满了欺骗和血腥的爱情。
恍惚间他竟想,自己也该被一同葬进坟里去。
假如那一天,毒性再猛烈少许,害得母亲暴毙而亡,陆家就会彻底倾垮。他的肩头不必扛起当家的重担,也不必再顾忌任何人的安危,可以孤注一掷地赌上性命,亲口向晏琛质询真相。
晏琛若服软,含泪说一句爱他,求他原谅,他就做一个丧尽天良的不孝子,扶棺葬下母亲,转眼抛却是非、承受骂名,继续陪着晏琛住在藕花小苑,与从前一般鹣鲽情深,年年岁岁雀成双,这辈子都活在一场清醒的、负罪的梦里。
晏琛若不爱他,狠心要报铲根之仇,就会用指粗的藤蔓一圈圈绕住他的脖颈,勒至窒息,生生扯断颈骨和四肢。临死前最后一幕,会是一场浮翠流丹的花雨,会是一双纯净清秀的眉眼。
铲根之仇源起于他,也终结于他。
待他死去,晏琛平息了仇恨,便还化作一株艳丽的夹竹桃,慵懒地绽放在藕花小苑里,汁液带一点儿甜蜜的剧毒,有心自保,无意伤人。
他在充斥着旧梦的孤坟里沉睡,晏琛在坟外作陪,春日里半眠半醒,迎着和煦的微风惬意摇摆。枝头的每一朵花苞都是他们的孩子,丝蕊含毒,花瓣热烈绽放,吐出一阵淡淡的香气。
如果结局是这样……该有多好。
伞梢悬雨线,道道织垂帘。绵延不断的流水声响在耳畔,寂清而空旷。
陆桓城维持着一个不变的姿势,在假山石壁上独坐了很久。他望着莲池对岸那一间风雨晦暗的屋子,总觉得窗纱会亮起,房门会打开,晏琛会穿着浅青的袄子,撑一把纸伞出来,又急又慌地奔至面前。
少年来拉他的衣袖,露出一截白皙瘦腕,偏又不敢使力,最后温软地说出一句:“外头雨大,你好端端的不进屋,怎么坐在这儿遭罪?”
他的嗓子太柔,连嗔怪也只含一分斥责,余下九分,尽显怜恤。
是南调啊。
分明是江南的水泽,江南的湿气,才养得出来的一口酥声软调。
他听了那么久,为什么始终不曾注意到?
初遇那一天,晏琛自称是江北嘉宁县人,可说出的第一句话就露了馅。他的语调和咬字是一场四月烟雨,竹叶尖儿凝出一滴清凌水露,滴在蚕丝锦缎上,洇入心窝,软绵绵地溶开。
陆桓城是阆州人,早就该察觉到——晏琛与他一样,生于阆州,也长于阆州。
是属于他家的一株花儿。
是他的花儿。
第四十一章 藏匿
“……你果真在这里。”
身后一声低语,被重重雨声阻隔,不甚清晰。
陆桓城心头剧颤,忙不迭地转头去看,只见陆桓康站在苑门处,伞沿压低,遮住了半张脸孔:“我刚才去探望母亲,你不在那儿,所以……我猜你一定来了这儿。”
雀跃的胸腔里才燃起一簇火,热意未浓,眨眼已被浇息。
他还在等谁?
时至今日,他怎么还能指望他亲自送走的少年回家?
陆桓城掩下失望,冷然问:“你找我干什么?”
陆桓康顿了顿,有些艰涩地道:“哥,你还恨我。”
“是。”
陆桓城干脆地承认,没有犹豫。
陆桓康持伞的手一抖,险些让风吹飞了轻飘飘的伞:“哥,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这五天,你不肯跟我说一句话,就好像……就好像是我害你没了晏琛!可杀人的、背叛的、坏事做绝的那个,难道不是晏琛自己吗?他险些害死母亲,却换得你一场念念不忘。而我呢?我戳破了真相,把你从温柔乡里救出来,凭什么要招你这样怨恨!”
陆桓康激动难平,五指紧握,几乎把伞柄掰断:“我看得明白,哥,我什么都看得明白。你恨的根本就不是我,是恨事与愿违,不敢承认你行商的精明放在识人之上,输得一败涂地!”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