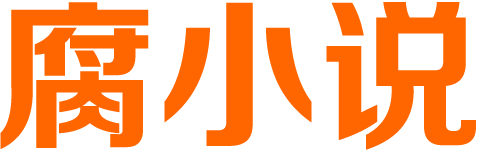西窗竹(5)
“啊!”
那握着门环的五指突然揪紧,晏琛面色惨白,呻吟着跪了下去,膝盖撞上尺高的门槛,险些栽进院子里。他慌忙撑住门槛,紧闭双眸忍耐,低哑而绵长地喘息。
笋儿只踹了一脚,他却不会只疼一下。
往往那一脚会踹得宫膜震颤,下腹收缩,然后忍疼时各种强烈的反应全扑上来,生生将疼痛拖得更长。晏琛好不容易熬到尽头,刚站起来,笋儿恰到好处又补了一脚,疼得他边发抖边腹诽道:这门难道克笋么,为什么死活都进不去?
陆桓城一觉睡饱,下意识去抱晏琛,却扑了个空。
枕边空冷无人。
他起身一看,晏琛正蔫蔫地窝在软榻之上,低着头,捧着茶水小口小口啜饮。厚实的狐绒氅子覆在小腹处,鼓鼓囊囊的一大团。
他悄悄摸过去,出其不意地揽住了晏琛的肩膀,往他脸颊上狠啄一口。
晏琛慌得洒了半盏茶,下意识伸手去遮小腹,抬头发现陆桓城笑盈盈的,没注意到他的异样,才软软地道:“桓城,你起来了。”
陆桓城倾身去吻他的唇,吻得唇面粘湿,呼吸微促。又顺着下颌蹭到耳根,叼住了绒软的耳垂,低笑道:“阿琛,怎么起得这般早?昨晚都舒服到晕过去了,也不多休息一会儿?”
晏琛耳根敏感,舔两下就忍不住要哆嗦,见陆桓城一起床就来撩他,忙不迭地往窗边躲。
陆桓城偷香得逞,心满意足,取了晏琛未喝完的半盏茶漱口,刚含进去,眉头猛地一皱,转身全吐到了地上:“你喝冰水?!”
“我……不怕冷的。以前,以前不是也喝过么?”
晏琛心虚地狡辩。
然而,他并不是不怕冷,是只能喝活水。
再嫩的茶叶,再甜的泉水,但凡经过烧滚烹煮,就失去了氤氲的灵气,变作一壶死水。像晏琛这般灵气汇聚的身体,死水只能解口渴,却解不了心渴。实在渴得难受时,他便会背着陆桓城偷偷舀些溪水、雨水饮用,之前被抓到过几次,都找借口搪塞了过去。
这几日积雪深重,晏琛寻不到流淌的活水,只能舀一捧新雪解渴。雪水性子太寒,他有些受不住,但总比渴死的好。
陆桓城紧紧捏着瓷盏,面容冷肃。
他扫了一眼桌上的茶壶,打开盖子往里一看,顿时脸都青了,一把抓起半满的茶壶递到晏琛面前:“你以前喝冷水,我不说什么,但这回壶里明明有水,昨晚剩下的,是冷了,是不怎么好喝,但毕竟放在屋里,总比外头的冰水强!阿琛,你到底有什么嗜好,放着茶水不要,非得去外面舀雪喝?”
晏琛连看都不敢看他,垂着头,双手在绒氅底下死死拧着褥子,双唇嗫喏,一个辩解的理由也编不来。
他怎么就疏忽了呢?
桌上有冷茶,他居然忘了倒掉,直接出去舀了雪。
怎么办呢?
狐狸露出了尾巴,被人揪了个正着,怎么逃呢?
半晌,陆桓城长长叹了口气,搁下杯盏,把晏琛按进怀里,手掌轻轻覆在那团绒氅上,温声道:“阿琛,你想喝什么都行,我不拦着。但是,你多少得顾念着孩子,下回再喝冰水,先含在嘴里暖一暖,别冻着它,好么?”
晏琛沉默一会儿,轻轻应了声。
公正地说,陆桓城并不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。
尽管行商的阅历和本能,会让他多多少少把值得推敲的细节挂在心上,可这种习惯,他从不带到与晏琛的相处中来,除非不合理的疑点太多,并且……没有一个曾得到过解释。
怀疑,或者说,仅仅是留意晏琛的举止,就让陆桓城感到了背叛的痛苦。
他不该对晏琛有一丝动摇。
世上既然有嗜茶成癖的人,自然也会有晏琛这样不爱饮茶的人,舀一盏春溪、山泉、初雪,权当痛饮天地灵息,未尝不是一种别致的闲情雅趣。
但当他这么劝说着自己,打开房门,看到一串从院门延伸进来的脚印时,那份竭力为晏琛保留的信任……终究还是碎裂了。
方才他抚过晏琛的长发,发尾隐约潮湿,那条漂亮的狐绒氅子垂在榻沿,不起眼的折角处几乎湿透。他便问晏琛,方才可曾出去过。
晏琛说,屋里烦闷,到院子里转了转。
当时那双眼里闪烁的不安,陆桓城并没有漏过。
如果打开房门,他看到的是两条足印,一条出,一条进,那么即使与晏琛所说不符,他也不会生疑,只当是院子太小,晏琛嫌闷,还出门散了散心。
但是,院子里只有一条归来的足印。
陆桓城这一夜睡得很熟,不知雪停、雪落各在何时,然而,一场雪要下多久才能彻底抹去新鲜的足印,他却是清楚的。
晏琛离开了很久,为了某个不知名的原因。
瞒着他。
在一场销魂的欢爱过后。
陆桓城很肯定,昨晚他的确把晏琛折腾得晕厥了过去,晏琛在床上向来脆弱,永远是一副无力反抗的姿态,绝无骗人的资本——被弄成那等狼狈模样,扶墙都站不稳,还要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溜出门几个时辰,晏琛到底去做了什么?
第五章 习性
晏琛站在马车旁,左手按氅领,右手扶车辕,慌慌张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他……上不去了。
从前撑着车辕,轻盈一跃便能上去,现在肚子鼓了起来,顶在前头,哪里还敢妄动。他左右换了几个姿势,比如屁股先蹦上横板,再把双腿带进去,可车帘外的横板太窄,他往后蹭得腰都断了,也没找到地方搁腿。
车夫看着他,眼神越来越古怪。
陆桓城今天先上了车,没像往常那样等在后头,随时准备扶他。
身体尚且灵便时,晏琛时常任性,嫌弃陆桓城小题大做,总把自己当做一个病入膏肓的人,搀扶的手伸到面前也不愿碰一下。现在陆桓城被他嫌弃够了,不扶他了,他却捂着肚子杵在这儿,连马车都上不去。
“阿琛?”侧帘被撩开,陆桓城探头出来,“怎么了?”
“……没事,我,我马上。”
晏琛连忙作出要登车的姿势,陆桓城瞧他似乎没事,便又把帘子放下。
晏琛偷偷松了口气,赶紧把腿收回来,揉了揉闷痛的肚子。余光瞥见墙边摆着一只木脚墩,简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,奔过去把那脚墩抱到车旁,安稳摆好,再扶住车辕,晃晃悠悠登上了车。
陆桓城坐在车里,撑着下巴看晏琛,觉得他今天怎么看怎么反常。登车磨磨蹭蹭,入座磨磨蹭蹭,目光瑟缩,窝进角落里便不再说话。还有那件狐绒氅子,平时不捆起来打死也不肯穿,现在却老老实实地主动裹在身上。
陆桓城凝眉想了想,释然地低头笑了。
晏琛偶尔会有几分小脾气,大约是自己哪儿惹着了他,正故意赌气对峙呢,晾一晾,气头过去就好了。他便悠然捧起一本书,靠在窗旁淡定翻阅,唇角带笑,时而往晏琛身上漫不经心地扫去两眼。
晏琛却并不是不想说话,他斜倚在软枕上,脑袋低垂,专心忍耐着腹中密密的钝痛。
实在太疼了。
笋儿一眨眼窜了两寸,腹部突然鼓胀,皮肤被拉扯得生疼,像刀子割了无数道看不见的裂口,连衣物摩擦都觉得痛。但和腹内的疼痛比起来,这又算不得什么了。可怜的宫膜还未扩张,硬生生被塞入一个两倍大的孩子,梨皮套在西瓜外头,几个月的苦痛聚于一夕要他承受,当真是有苦难言,咬牙都来不及,哪还顾得上说话。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