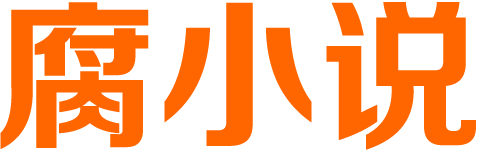秘密星河(28)
光是听他描述,梁迁的心已经揪成一团,急切地问:“怎么样,能检测吗?”
“能是能,”段星河又沉默了。他讲报警这一节的时候,迟疑、停顿的频率比先前更高,似乎在经受什么难以启齿的煎熬,过了一会才说:“做了DNA检测,但是公安部的资料库里匹配不到吻合的数据。”
梁迁明白他的意思。这意味着,强奸段小优的男人或者是初犯,或者是手段娴熟、屡次逃脱法网的惯犯。
“当初就不应该报警。”段星河忽然转过头,用后脑勺对着梁迁,好像鼻塞一样,声音闷闷的,“都是我的错。”
“别胡说。”
段星河执拗地重复:“就是我的错。”
“段星河,你别这样,”梁迁捏住段星河的肩膀,稍微使了点力,“你转过来。”
段星河似乎有些醉了,勉强挣扎了几下,很快被梁迁扭转回来,微微张开嘴唇,眼神迷离地看着他。
“你没有错,你妈妈和小优也没错,错的是那个强奸犯,你明白吗?”
见他不回话,梁迁屈起食指,在他额头上敲了一下。段星河像个玩偶,随着梁迁的动作晃动,可能是觉得梁迁严肃的表情很滑稽,他忽然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容:“我知道。”
他怎么会不知道呢,道理他都明白,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懊悔,就像控制不了当初吃人的舆论和急剧恶化的事态。
被寄予厚望的DNA鉴定没有抓住强奸犯,段小优却在漫长的调查取证中精神崩溃了。一连数日,她面对着一双双充满同情的眼睛,不断地回忆和讲述被强暴的细节,还要回答那些尖锐的提问——虽然它们本身是善意的。
你呼救了吗?为什么喊不出来?他用什么东西堵住你的嘴,什么东西捆住你的手,用什么姿势插入?一开始她总是哭,后来渐渐麻木了,明亮的眼睛变得呆滞而无神。
每次做笔录,段星河都陪着段小优,有时他搂着妹妹消瘦的脊背,哀求对面的警察,别问这些了行吗?
可是不行啊,他们要查案,这些细节是必须要知道的。
不到两周,段小优就瘦得形销骨立,她常常把自己锁在卧室里,谁叫也不答应。段星河每次用钥匙开门都提心吊胆,生怕看见空无一人的房间和一片随风飘舞的雪白窗帘,进门的时候也总是神经质地用鞋尖碾一碾地板,看看是不是踩到了什么粘糊的液体。
在段小优陷入抑郁的同时,孙娟的状态也一落千丈,原本滋润丰满的身体干瘪了,脸蛋变得蜡黄憔悴,整夜失眠,呆呆地坐在阳台边上。女儿遭遇了暴行,本来应该从她这里得到最大的慰藉,可是孙娟精神恍惚的程度竟和段小优不相上下,甚至有点害怕靠近小优,除了事发那天抱着女儿痛哭一场,连平日里的嘘寒问暖都忘记了。
沙发垫被送去检测精斑后,孙娟的焦虑更加明显,一天要问段星河十几遍,有结果了吗。后来听说DNA鉴定抓不住罪犯,孙娟气疯了,在公安局里静坐、闹绝食,一口咬定强奸犯是某个住在附近的流氓,让警察把他抓起来。
闹了许多天,民警不堪其扰,让段星河把孙娟劝回去。他们调查了,段小优出事的时候,那伙流氓在街边打牌,附近的居民都看见了,有不在场证据。
可是孙娟不信啊,怎么说都没用,那时候她的精神已经开始出现问题,偏执到疯癫,竟然拿着菜刀要去找人家报仇,就在红枫路那棵上百年的榕树旁边,差点闹出命案。
一半出于谨慎,一半出于无奈,民警将经常活动在红枫路一带的那伙人全部带到派出所问话,还要求他们做了DNA检测,结果,没有一个人与罪犯的基因信息相匹配。
那伙流氓平日里就爱胡搅蛮缠,这会被冤枉了“清白”,更是咋咋呼呼,得理不饶人,嚣张的气焰差点把公安局给点了。他们回到红枫路,站在段星河家楼下指桑骂槐,不堪入耳的脏话一串接一串,引来无数路人的围观。本来段小优被性侵的事,只是自己家里的秘密,被他们这么一闹,一下子方圆五里无人不知。
孙娟情绪激动,面色紫涨,走到窗边想与他们理论,刚要开口就晕倒了。段星河接了一桶冷水,“哗”地从阳台上泼下去,然后将孙娟抱到沙发上,掐她的人中。
那伙流氓聚集在楼下,跳着脚骂了一个多钟头才渐渐散去,孙娟醒来后,一直默默流泪,突然惊天动地地咳嗽一声,吐出一口带血的痰。
而几米之外,段小优的卧室房门紧闭,安静得像一座坟墓。
那段时间,段星河从来没有真正睡着过。他时刻保持警惕,做梦也留着一线意识,孙娟和段小优制造出的任何响动都让他恐惧,如果什么响动都没有,又是另一种恐惧。
偶尔也有熬不下去的时候,有一天,段星河质问孙娟,妈,你能不能坚强一点?你明明是那么坚强的一个人。
孙娟在喝米汤,手中的汤匙掉在地上,摔碎了。她神志不清地扑到段星河身上,叫嚷着“你去死吧”,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。
她的力气异乎寻常的大,段星河涨红了脸,精疲力尽地与她撕打,因为呼吸紊乱,额头上渗出层层细汗。
多日不见阳光的段小优,穿着布袋子一样的睡衣,像女鬼一样飘过来,帮助段星河拉开了发疯的母亲。
孙娟看到段小优,整个人定住了,过了几秒,忽然抱住她号啕大哭,颠三倒四地说妈妈对不起你。
段星河花了很多时间盘问,因为孙娟的精神状态不能集中,记忆也出现了问题,他费了好大劲才弄清原委。原来那天晚上孙娟回家时,曾在楼梯上与一个男人擦肩而过。老楼里很黑,一楼还有一盏十几瓦的灯泡随风摇晃,到了四五层,便只有破窗而入的月光照明了。
孙娟走到四层半,在楼梯拐角的平台上,跟一个行色匆匆的模糊人影撞上,那人戴着口罩,低着头,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,听到孙娟说“对不起”,还应了一声。
孙娟患有类风湿,平日里行动不太利索,揉着后腰慢慢爬上楼,到了自家门口,忽然听到断断续续的、沉闷的呜咽声。她觉得奇怪,掏出钥匙开了门,借着幽暗的月光扫了一眼客厅,几秒后,控制不住地尖叫起来。只见段小优蜷缩在沙发上,赤身裸体,嘴里塞着内裤,正在剧烈地发抖。她的双手被缚在背后,雪白的乳房上布满了暗红的掐痕。孙娟捂着嘴,踉踉跄跄地下楼去追,但是耽搁了几分钟,外面车水马龙,灯光绚烂,强奸犯已经找不到了。
孙娟很爱很爱段小优,这份爱太重,最终变成一个名为愧疚的巨大漩涡,将她拖入了黑暗深渊。
段星河同时照顾两个抑郁的病人,精神高度紧张,脱发、暴瘦、黑眼圈牢牢地粘在脸上。许多次他濒临崩溃,全靠意志力撑着,反复告诫自己不能放弃,否则这个家庭就真的垮了。
所幸,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,段小优慢慢恢复了健康。她开始主动进食,也会帮着段星河打扫卫生,但是性格完全变了,变得胆怯、神经质而且沉默。在她好转的同时,孙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,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,段星河跟段小优商量,搬到沧市去,把母亲送到清沐疗养院治疗。段小优神色木然地点头,顺从地接受一切安排。
她也不得不走,流言蜚语是传得最快的,不说街坊邻里,就是在学校,她被强暴的消息也已经人尽皆知,段星河去办转学手续的时候,就有某些学生围着他指指点点。
于是,在暴行发生三个月后,他们搬到了沧市,一个繁华、陌生、举目无亲的地方。抵达的当晚,段星河看着银行卡上的余额,咬牙做了退学的决定。他没有别的办法了,家里的存款有限,而孙娟的治疗费用高昂,最重要的是,段小优离不开他。
于是就这么生活着,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之后,段星河回到渔州,在一个霞光万丈的傍晚,遇到了他的老同学梁迁。
“就这样。”段星河又喝完了一杯红酒,眼神有点飘,对梁迁露出一个很淡的笑容。
“你是不是醉了。”梁迁试探着搭了一下他的额头,觉得有点烫。
上一篇:楚天以南
下一篇:嫁进豪门当男妻后我红了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