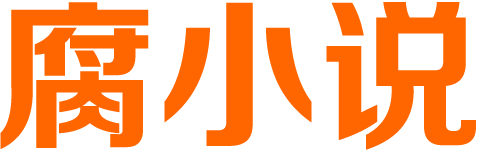共生关系(19)
他的手指白皙且骨节分明,搭在玻璃上向外看的动作无比熟稔,像一幅工笔静态图,似乎是从无数相似的时间节点里被提取又打乱顺序,在我不曾触及的过往中重复描摹了千百遍,任意选出其中之一呈现在眼前。
他是孤零零的旁观者,他是一块真正的玉,大隐隐于市,却仍旧带着它自深山开采出前不识万物的骄矜。
只是美丽的事物往往脆弱。
占有意味着从属,人心是关押欲望的牢狱。字字相嵌的教条只能编织出虚构假象,刻在基因里那些顽固才是掩饰无能的真实。我当了十几年的正常人,成为变态只需要瓷器与大理石地面碰撞的那一瞬间。
圆形轨道不知疲倦地转动,视野逐渐攀升,唐幺转过头来看我,眼里溢出笑意,手指无意识地微微蜷缩起来,咬咬唇,无声开合。
大概是叫了我一声。
“大概”是因为,感官中那几秒似乎陷入一种轻浮真空,介质缺失消融声音,鼓膜只隐隐附和上某种隐秘而澎湃的震动。
电话铃声突兀响起前的那一瞬间,我感觉到自己手指轻微动了一下。
空气重新涌回来,唐幺像是被惊回神,眨动两下眼睛,往我一侧衣兜看过去。
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,秦章。
我把手里零食递给唐幺,按下接听,“什么事。”
秦章言简意赅,短短几分钟内叙述完他如何凭借一己之力迅速解决问题,同时搞定了新投资方、施工队、汤恬恬和钱复来。
我没听明白最后一句:“跟钱导有什么关系?”
秦章咳了一声,“新金主带资进组。”
我皱眉:“这他能答应?”钱复来这人脾气怪得很,平时话都懒得跟人说,一拍片子就开始护崽,谁瞎碰跟谁急。
秦章幽幽道:“不止。当场拟合同,就差两眼冒光抱着人喊‘缪斯’了。”
我想了一下:“你给他拉了个三栖影帝过去?”
“不,”秦章说,“是晋长斋,你还有印象吗?他跳槽过来了,自费解约,往组里投了两百万,面的角色是苏掾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“就是那个活在绅士回忆里早八百年就死了的恋人,我去钱导那瞟了一眼,拢共三句台词五次出场。我怀疑他要么这些年磕坏了脑袋,要么……”
话说一半秦章突然挂了电话,接着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:“要么晋长斋八成是想睡你,你千万小心点。”
我手指顿了一下,带着清清楚楚的备注截图,让展岳转发给晋长斋。
唐幺能跟我这么久,除了性吸引力高得莫名外,最重要一点是乖觉,该安静时从不闹人。见我锁了手机放回兜里,才捏了块炸薯喂我。
摩天轮缓缓转过大半圈,照进来灯影角度逐渐倾斜,将他半张脸藏进暗处。我微微倾身去咬,嘴唇在他指腹上一触即分。他把手缩回去背到身后,抬眼偷偷看我。
出观光厢时我扶了他一把,“还坐吗?”
他摇摇头,借着夜色掩饰悄悄握住我手指,捂着肚子小声说饿。我“嗯”了声,开车带他去了上次没吃成那家粤菜馆。
白日里看着再亲密登对,唐稚和我终归也不是一类人。
就像刚刚在摩天轮上,他看我的眼神情意缠绵,只想讨一个最高点的亲吻。而我跟玻璃中倒映的无数个我却只想撕裂他的衣服,扯住他的头发往冰凉观光窗上抵,肏进他的身体,在身上咬下独属我的印章。让他又冷又热,痛得挣扎,流泪也流血。
第23章 08
错觉让你永远分不清楚这是心动还是情动
那天晚上唐幺乖得很,身体柔软温热,比平时更容易摆弄,也来得更有感觉。单是光着身子坐在我怀里接了会吻,就开始硬得淌水,扭着腰直往我手上蹭,激起我一点儿久违的暴虐欲来。
我掐着脖子把人按倒在枕头上,垂眼淡淡看了他一会儿,俯身在他水汽朦胧的眼睛上亲了下。
人在漫长的进化期里摆脱了繁衍交配的发情期,又能在一个眼神中被轻易唤起幕天席地下交媾的本能。
他的身体变得酥软,像浸在情欲中被泡发开,连吐息间都缠上潮湿意味。那种潮湿是盛夏沙滩或者热带雨林,吸引水汽造访又得温度眷顾,触碰肌肤凝成浓郁到化不开的荷尔蒙。
唇齿间漫起轻微的血腥味,我松开手把他拉起来,从床头道具柜里拿了副软皮手铐,将他两只手束缚在身后,退开一点儿看他。他看着我,嘴角还带着未干的唾涎和血丝,慢慢眨动几下眼睛又乖乖闭上,分开大腿跪坐在床上,开肩挺背,露出柔软的胸腹。白得像籽玉,隐隐透出淡青色纹路,缀着两点红缨。
唐幺的身体……唐幺就是性欲本身。
血管中有什么东西点燃炸开,火花顺着一路流窜进心脏和大脑。情欲本身就带有侵略的意味。
牛皮散鞭在他胸口处斜斜打下第一道微红痕迹,乳尖受到刺激开始充血挺立,唐幺身体轻微抖了下,发出撒娇催促的鼻音。
打一下,要亲一口。
我倾身托住他侧脸,安抚地缠上他舌尖。
偏于调情作用的散鞭在唐幺身上能引发足够的疼痛刺激,不出几下就能让他成熟艳涨,汁水淋漓地绽开。
我俯身亲了亲他胸口,绕到身后替他解开束缚,戴好套,掐着腰操进他身体里,在高热肠道收缩推挤中慢慢顶送。
大概是跪得有些久,他双腿支撑不住,在被顶撞得不断往前挪动时身子一软伏到床上,趴在那没了爬起来的力气。我跟着贴住他身后,把他整个压在身下顶弄,眼眶发热,手掌和牙齿在他后背光滑软腻处留下深浅不一的红痕。
做爱时胸腔会强烈擂动是人类最卑劣的骗局,错觉让你永远分不清楚这是心动还是情动。
他被压在床上呜呜噎噎挨了一会儿操,突然挣扎着反手胡乱来摸我,我动作没停,捏住那只手腕用指腹摩挲,“怎么了。”
他侧过一点脸来,吸了吸鼻子,“……磨得好疼。”
我继续往里插弄了几下,撤出来,直身拉起他靠进怀里,去摸他胸前和小腹。
鞭笞开拓出充分热辣敏感,又贴紧跟床单不断摩擦,他身前遍布红潮,乳粒充血肿大微微发颤,被我一碰就疼得直躲。
我托着他转了个身,面对面在我怀里往下坐,敞开身体让我重新进去,咬着耳朵笑他:“娇气。”他不理会,缠着贴在我身上,只管往我颈侧亲,呻吟触碰里全是赤裸裸的勾引。
脱下衣服的同时也要一并扔掉理智,这才是对床笫之欢最基本的尊重。剥离社会属性附加的一切约束,残留下本能的本质尽是欢愉。
我跟他相拥陷入这欢愉中。
扔掉第三个套子时,唐幺已经在疼痛和情欲的双重折磨下没了力气,大敞着身体,一条腿从床边耷拉下去。
他的身体被激起全然程度的敏感,随便往哪里轻轻碰一下都反应剧烈地无意识痉挛,鼻腔里轻哼出呓语般意味不明的低喃,眼睛茫然睁着落在虚空一处,生理泪水还在痴痴往外淌。
我带他去浴室清理完身体,又抱回床上用被子裹住,等搂在臂弯抽完一支烟,他才往我肩头蹭了几下,缓缓回过神,伸手要来够我刚点上的第二支烟。
我吸了一口,松开牙齿让他拿走,垂眼看他拿着凑到自己唇前,含在嘴里抬头看着我笑。
我往后靠了点儿,让他躺在我腿上,拿下医药箱给他清理红肿破皮的地方。
处理完上半身,我把他托起来倚靠在床头,他没什么劲儿地往旁边倒,又被我重新拉起来,在两边塞了几个枕头撑住。
他膝盖处刚刚在床上跪出一片磨红痕迹,大腿小腿随处是我捏出的、咬破的、撞重的、不知道在什么上磕出的淤青,有些微胀红肿,有些还在隐隐往外渗着血丝。
我坐在他两腿间,握着他脚踝把一条腿搭在身上,用棉签沾着碘伏给伤口消毒。那些青红驳痕横亘在他光洁脆弱的大腿内侧,我突然莫名烦躁起来,手上动作不停,绷着情绪淡淡开口:“唐稚,你现在带着这一身去报警,说不定能鉴定轻微伤拘留我十天。”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