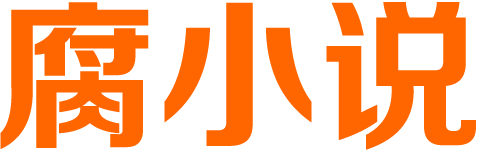重生后我佛了但渣男们都开始慌了(115)
这个节骨眼上要出去,燕母可是特意交代过看着他点,福顺眼皮狂跳:“公子,您要去哪儿?夫人说您最好不要出去。”
燕挽一默,稍微冷静了点儿,心想他当真是气糊涂了。
然而,这口气是如何都吞咽不下的,他大步他踏出了门槛,环视了一圈四周,高声道:“我有事想见太子殿下。”
四周毫无动静,但燕挽知道话一定会带到,转头就回了房。
果不其然到了晚上,有人潜进了他的厢房,黑漆漆中一把搂住了他的腰,将他禁锢在床榻上,嗓音华丽而富含磁性:“挽挽想我了?”
燕挽冷冷推开他,坐了起来,叫人进来点灯,待得室内灯火通明,宁沉看到燕挽神情不佳,才感不妙,薄唇弯曲的弧度不经意间浅了一下,甚至连声音都染上了自己没有察觉的轻哄:“怎么了?谁又惹我的宝贝挽挽生气了。”
燕挽将匣子搬过来,将里面的信件扬了一床,问:“是不是你?”
宁沉终于知道燕挽这股火气哪儿来的了,事情已经败露想打死不承认是不可能的了,就只能低声下气求原谅这样子。
“是我。”
燕挽活生生气笑了:“宁沉,你怎么这么无耻,什么都干得出来。”
拦他的信也就罢了,还伪造字迹骗他,不愧是皇家的人,弄术的手段无人能及。
宁沉分明理亏,却毫不心虚,反问:“难道你要我看着你同别人书信传情,情意渐浓,不可收拾?”
燕挽气红了脸:“那你也不能如此作为。”
宁沉继续追问:“那该怎么作为?”
他闭着眼,冷冷道:“我羽翼未丰,怕尔虞我诈伤及你,不敢向你袒露心意,我不能向宋意一样,若有似无的勾引你,不能向祁云生一样,撞柱以表决心闹得满城风雨,我要等,等一个最好的时机同你长相厮守,还要保证在出手之前,你的魂儿不被任何人牵走,你倒是教教我,我该怎么做才好?”
燕挽一噎,火气消散了一丝,无奈又缓慢地说道:“你这样让我怎么对得起云生?”
时隔这么久,斯人已故,他才发现其中蹊跷,怪不得在他提及书信时,祁云生会表露出错愕,原来他的回信他根本没收到。
他就这样在他单薄的寥寥的回应中爱了他这么久。
宁沉闻言睁眼,眼神深沉的,一字一句地问他:“你觉得自己对不起祁云生,那你又可曾对得起我?”
“燕挽,我感觉得出来,你是喜欢我的,哪怕以前你对我避之惟恐不及,你心里也有我一席之地,为了一个祁云生,你还要无视自己的心意多久?”
“你将我置于何处?”
燕挽一派错愕,脑子忽然一片空白。
宁沉直直的盯着他:“你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,我密谋布局良久押的这一场豪赌,不会输。”
第116章 难嫁第一百一十六天
自信狂妄到了极点。
他又往前走了一步, 逼近他:“你敢回应一声不是?”
燕挽往后退了半步,慢慢的带着一丝茫然地说道:“但你这样分明是不对的。”
宁沉扣住了他的手腕,那是青色血管隐约可见的皓色一截,他用沉沉的语气说:“我不能让别人成为你的寄托。宋意负了你, 我才是那味药, 祁云生捷足先登, 我恨毒了他, 倘若能够使你不喜欢他,再过分的事我都做得出来, 我喜欢的人我要紧紧攥在手里,不能让别人夺了去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攥得太紧, 就会变成伤害。
他有底气亏欠他们当中任何一个,唯独不想亏欠祁云生,却还是欠了。
“挽挽。”他收紧了手, 勒得他手骨都疼,好像生怕他跑了一般, “是你跟我说谋事在人, 成事在天, 有想做的事一定要去做,有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努力去争取, 你不可以怪我。”
燕挽失去了任何言语,也再没有半点怒火, 他只感觉到一阵深深的无力,原来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命运的安排。
“殿下,没有人能容得下我们的。”
孤注一掷, 并不值得。
宁沉忽然不想听了, 一只手掐住他的腰, 另一只手顺着他的手腕爬到他的指缝里去,与他十指相扣,吻了下去。
他纠缠着他的唇舌,光滑的下颌曲线被镀上了清辉,然后探到了他的衣领里,指尖擦过他的颈边。
燕挽还念着蓝佩,推了推他的肩,当意识到宁沉的越界,他猛地呆住,然后剧烈挣扎,并从唇齿间偷出一丝空闲,喘息着唤:“殿下,别。”
却不过是更加加深了宁沉的浓沉之欲。
片刻,室内发出一道裂帛之声。
宁沉欲抱燕挽入帐,不慎踩了一块帐尾,不耐烦中,干脆挥手将半边帐幔直接撕开,随后另半边帐幔掩下,里面抛出一条腰带。
燕挽被细密的亲吻着,说出的话总是被掐准了时机堵了回去,他攥紧了宁沉的衣襟,反被男人束住了手,男人跪伏在他身上,眼眸猩红。
宛如蓄势待发的狮子一般,他嗓音沙哑道:“挽挽,给我。”
燕挽与他对视,望进他汹涌着暗欲的眼眸里,眼眶蓦然发热:“殿下,万民会骂你的,百官也会。”
宁沉却充耳不闻,额头上覆了满满一层薄汗,又一次道:“挽挽,给我。”
纱帐中火热气氛已至顶点,仿佛拉紧的一根弦,随时会断,宁沉弓紧了背脊,隐忍着等着燕挽的回答。
良久,燕挽道:“倘我今天给了殿下,能不能请殿下今后与我两两相忘?”
宁沉眼眸一凝,恨恨咬牙,片刻说“好”,燕挽主动坐了起来,伸手抱住了他腰。
痛意弥漫间,燕挽咬了他的肩膀一口,犹如濒死的鱼:“殿下,说话算数,回去之后不要再同陛下闹了,以后你有良臣万千,万里江山,一定要做个明君才好。”
宁沉简直想将他弄死,单手扣住他的下颌,迫使他抬头,狠戾又阴沉的冷笑:“我当然说话算数,同你两两相望,未来千万个日日夜夜,我们一同从榻上醒来,我都会如此时这般望着你。”
燕挽眼底弥漫出一片错愕,接着脸色大变,意识到自己中了宁沉的陷阱。
他想后悔已然来不及,宁沉好不容易勾到手的人怎肯轻易放过,再度吻下,势要让燕挽步入极乐之境。
一场漫长的索求几乎持续了一夜。
次日,宁沉醒了个大早,燕挽却还在睡,他的睡颜惹人怜爱,令得他不由俯身垂下头去。
昨天太过生气,一时没克制住发了狠,光洗澡就用了半个时辰,桶里的水撒了一地,几块木板都松懈了,燕挽哭个不停。
他累了自得好好休息,宁沉悄无声息的下床,穿好了衣服,然后推开门出去。
院外洒扫的画莺见到宁沉陡然一惊,忙上前去行礼,宁沉道:“同你家公子说,我走了,明日过来向他赔罪。”
画莺应是,宁沉顷刻远去。
如今正是紧要关头,宫中不能没有他主持大局,他要提防着天子对燕挽下手,随时掌握第一手消息,临走前特意留下了影卫。
而当燕挽醒时,已然日上三竿,身边不见宁沉的人,画莺跨进门槛欲像往常一般伺候,倏地听燕挽道:“出去。”
“公子?”
画莺疑惑着退出了门外。
燕挽吩咐她:“换福顺进来,顺便命人抬桶水进来,我要沐浴更衣。”
画莺照办,换了福顺,福顺昨晚守夜,对发生了什么心知肚明,进去后看到燕挽身上的吻痕没有半点大惊小怪,他还特意关怀道:“公子,不如私底下偷摸找个大夫来看看吧,免得身体不适。”
燕挽说了声“不用了”,然后咳了起来,他喉咙嘶哑,宛如干涸的麦田,灌了水也不顶用,这才发现自己有些发烧。
额头温烫,好似也不是特别严重,燕挽说:“取我的笔墨来。”
福顺顺他的意取了笔墨,只见燕挽提笔写下几行字,然后递给他:“送去蓝府。”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