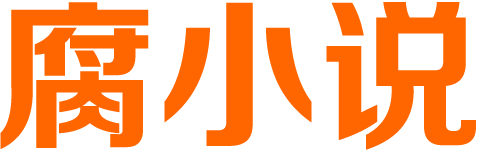以撒怎么了?(61)
第52章 自白
“开始,那只是一个意外。”
罗伯特说。
1916年,战争还没有结束。虽然在英国本土的人们不是很有战时的实感——然而,老罗伯特还是因为听闻了某场惨烈的会战而彻夜难眠。那时候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体面的天主教修道院院长,手臂上只有松弛的皮肤和老年斑,而没有发肿的针孔。
“我是一个很守旧的老家伙,”他说,“修道院就应当时刻保持其纯净。我赶走过很多被不知悔改的年轻人,房间总是住不满……最开始,仅仅这样的,我没有——曾经,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思。”
因为辗转难眠,虽然当时修道院实行宵禁,但身为院长的罗伯特还是决定起身出去走走。
“我一路走到天井。”
罗伯特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。他原以为是猫,走近了,眯起眼睛一看,惊觉矮墙上攀着一个人——准确来说,是一个修女。她的裙摆被挂在了树枝上,极不端庄地露出了大腿这种隐私部位。
他愤怒而羞赧地别过脸,低声斥责:“不论你是谁,看在主的份上,还不赶紧下来!”
黑暗中,那修女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,反而一脚跨过墙头,使劲扯着被勾住的裙摆,想要干脆翻到外面去。
“您就忘了我吧,”她头也不回,“我受够了!”
这两句话里的每一个单词都把罗伯特刺痛了。他自认为没什么做得不好的,什么叫作受够了?另外,他隐约回忆起了那些修士修女背着他讨论的风闻——他想,无论事后如何处置,现在绝不能任由这个修女翻出去撒野。
“情急之下,我抓住了她的脚踝……”
“放开我!”那修女恼怒地回过头,想一脚把他蹬开,又顾虑他是个老人,于是她放软了声音低声求情,“我会就此悄悄地离开,到很远的地方去,离开这个教区,永不回来。院长啊,人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爱情,我不得不去!”
“太荒唐了!泽维尔先生……你简直想象不到,听到这话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震撼。但是,我也不希望声张这种丑闻。所以一开始,我只是劝她。”
“说的什么胡话!你曾读过的经书是这样教导你行事的吗?”院长紧紧抓住她的腿,听见她发出一声痛呼,“爱是恒久忍耐,又有恩慈;爱是不嫉妒;爱是不自夸、不张狂,不做羞耻之事,不求自己的益处,不轻易动怒。不计算人的恶,不喜欢不义,只喜欢真理;凡事包容、凡事相信、凡事盼望,凡事忍耐;爱是永不止息……什么样的爱像你这样愚蠢浅薄?回头吧!回到你的房间里去,这件事还有商榷的余地。”
修女的眼眶湿了。然而,她极缓地摇摇头,挣开了罗伯特的手,蹲在墙头上,随时准备一跃而下,她身旁的树枝还挂着一缕飘荡着的布料。
“但是害死她的不是我,是一只猫。”
“猫?”
猫。修道院有很多游荡的野猫。有一只格外亲人的,一跃跳上墙头,尖利地叫了一声,像婴儿的啼哭。修女被吓了一跳,重心不稳,她向后仰倒——
随后是一声短促的惊叫。
“她倒下的时候,我躲开了。
“也许当时我接住她,或者仅仅是给她垫背,她就不会死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,近乎一种逃避危险的本能?主啊,我知道那个情景——她仰面倒在地上,血从后脑勺晕开——将伴随我的余生,如影随形。”
“你有尝试救她吗?”
“有。我用手帕捂住她的伤口,但是血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出来,顺着我的手臂流进袖子里。她的脖子呈现出怪异的弧度……”
泽维尔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但这只是个意外,不是吗?”
“从事实上说,是的,”院长说,“然而,我的身上有她的血;她的脚踝上留有我五指印下的红痕,没有任何即将消退的迹象。我太害怕了,或许有人看见我离开房间?或许——我,院长罗伯特,要被当作杀人犯?”
罗伯特把尸体轻轻放在地上,血已经不再涌出。他的视线有一瞬间的模糊,心脏剧烈的震颤和急促的呼吸声清晰可闻。他的耳朵在发烫。
猫跳下来,远远地嗅了嗅尸体,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,在舔爪子。罗伯特怕它身上沾到血迹就会暴露自己,生平头一次摆出凶恶的表情,把它吓跑了。
窸窸窣窣,枝叶摩擦的声音像很多人在低语,像杂乱的脚步声。
“必须要在天亮之前解决这件事,我是这样想的。我注意到了那个还未完成的地窖。我把她连同带血的泥土一起埋下去,在旁边重新挖了一个浅坑,第二天,没有人注意到地窖的位置发生的变动;没有人想到她出了意外,只以为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终于选择出逃。”
“你做噩梦吗?”泽维尔问。
“每天。”罗伯特说。
“我一直觉得她的鬼魂还在修道院里。那修女死后不久,加文突然感染了风寒,高烧不止,我以为这是她的报复。我们雇了马车把他运下山去,一路上我都在祈祷。这孩子随着马车颠簸着,灼热的呼吸洒在我的手上,我由衷地想,只要有机会,我愿代他去死;只要有机会救他,我敢做任何事……
“修道院没有钱,我也没有,我们只能去公立医院。加文被医生推走了,我坐在走廊里,不知道后续要花多少钱,不知道日后该怎么办。我的心中隐隐有些不安,不只因为身无分文。
“然后,有一个人站在我面前,说:‘你想必就是罗伯特院长吧。’
“我抬头看他。”
泽维尔屏住呼吸,院长也没有说话。他的两手放在膝头,摊开,盯着掌心看了许久,攥紧拳头,苦笑着摇摇头,像否定了那之后的所有人生:“他提出的要求和给出的承诺,我都全盘接受,他给了我一笔钱,加文用了药后,高烧很快退了,但那深渊是不可抽身的。从抗拒到依赖没有用掉我太多时间,也许从本质上我也只是一个软弱的、容易沉沦的人。我手上的每一针、每一笔另作他用的捐款,都在把我往下拉扯……修道院变得越来越富有。大家看见足量的面包和黄油都很高兴,没有察觉什么不对。可笑的是,唯有这些事才能让修士们健康起来,才能阻止死亡的灰马带走加文。”
“那么第二次,还是意外吗?”泽维尔问。
“第二次?”
“第二个死者。”
罗伯特院长难堪地避开视线:“……每次注射‘药’之后,我像被魔鬼附身,完全变了一个人,事后反而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。”
“可是您的行事却谨慎且缜密,”泽维尔说,“所有死者在死前都有相同的情况:在向您告解之后,露出飘飘然的愉悦姿态。你给他们也注射了所谓药物,你否认这点吗?”
“……”
“你还留着你的‘药’吗,哪怕一点点?或者你能知道它的名称?”
院长摇摇头:“每次都是那人带来给我。”
“你后来还做噩梦吗?罗伯特?”
“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”
泽维尔叹了口气:“在这期间,你始终帮那个人做账?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么账本——”
“请别问了,侦探,别深究这件事,这是为您的安全着想。不过,我可以告诉您,在您因病离开后不久,他就亲自前来带走了账本。”
“嗯,”泽维尔说,“对我下毒的事,是你的主意还是那个人的?”
“不是我。”
“你这样受他控制就没有不甘?既然可以对修士下手,自然,他也……”
院长惶恐地抬起头看了泽维尔一眼,用力摇摇头:“我做不到。”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