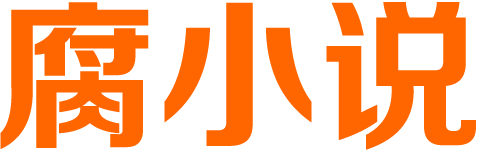戏装山河(175)
沈培楠被他噎得说不出话,莫青荷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掏出一支粉红色玫瑰花,用柔软的花瓣扫着他剃得锃青的下巴:“以前赶得时局不好,你带着兵作威作福的,没正经傍过戏子吧?按我们的规矩,我唱到夜里几点,你的车子就要在戏院外头等到几点,给不给好脸色得看我心情,包够了两三个月的场子,才能换来我列席陪一杯酒。”
“喏,刚才一位外国戏迷送的。”莫青荷将玫瑰花往他手里一塞,“等了我一晚,陪个不是。”
“反了天了,可真是把你惯得反了天了,你尽管忙去,我不管谁傍着你、多少人捧着你……”沈培楠被他气得哆嗦,把那玫瑰重重掷在地上,推开他率先大步上了楼,莫青荷紧赶几步,收敛了脸上的笑意,“沈哥,沈哥!”
那漂亮极了的声音在身后回响,沈培楠神使鬼差地走慢了一步,莫青荷撵上来,抬起一条胳膊搭着他的肩膀,无视沈培楠杀气腾腾的表情,偏着头、踮着脚,硬是讨了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, 声音温柔了下来:“一句俏皮话也禁不住,不像我认识的沈军座了。”
沈培楠别过脸不说话,下颌角的线条格外生硬:“小莫,我不反对你的事业,但你和那个莫柳初,过分了。”
莫青荷花了好一阵子才顿悟了他这番话里的意思,低头沉吟片刻,眼里就浮出一层柔和的爱昵:“吃醋了?”
沈培楠被说中心事,无端受窘,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才能挽回尊严,喉结上下滑动,突然用力扯了扯黑色睡衣的领子,骂了句什么就要走。莫青荷赶忙拉住他,竭力憋着笑:“沈哥,我从不知道你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”
他往沈培楠身前靠了靠,解下颈上宽阔柔软的开司米围巾,轻柔的缠住他们两人,也挡住了赶来看热闹的南洋佣人们的视线,在这温暖溽热的方寸之地里,仰起脸亲吻沈培楠眼角的细纹。
他抚摸沈培楠温热的后颈,用呢喃般的絮语安抚他:“沈哥,太忙的是你,现有的生活已经足够,不需要更多的金钱,你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来戏班子看看我在做什么。”
“戏是有感情的,我唱得每一句,都在对你倾诉我的爱意。”
从那之后,沈培楠真就有了空闲,他把举办宴会和跟生意伙伴打牌跳舞的时间腾出来,动不动就往莫青荷的戏剧学校跑,原先他爱旧戏,只是爱戏台上的光鲜和旖旎、爱戏里人的惺惺作态,现在才知晓了台上唱念做打背后的苦功夫。
戏是苦差事,莫青荷穿着白布衫和蓝色灯笼裤,自顾自压腿练声,“拧旋子”、“飞脚”、“拿顶”、“小翻”,气喘吁吁,全身被汗溻透了一遍又一遍,背后碱出了白茫茫的盐粒,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滑到下颌,沿着下巴尖儿啪啪的往榉木地板上砸,连那密匝匝黑漆漆的睫毛都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,仍是端着腿一动不动。有小小的孩子背不出戏词,莫青荷擦一把脑门的汗,蹲下身子,柔声一个字一个字给他讲解戏里的意思,讲明白了,自然而然的也就记住了。
练功房热热闹闹,有练踢腿的,有练倒立的,也有三三两两的孩子坐在角落喝水休息,一人抱着一只本子,煞有介事地念: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一会又蹙着眉,自言自语:“……门泊,门泊是什么意思?”
一般长在异国的孩子要保持中文水平实在太难,中文数月不用就连语法都颠三倒四,这里的孩子能背诗词,大一点儿的孩子,讲起论语也煞有介事。
沈培楠心疼莫青荷,趁着排练的间隙叫他过来,帮他捏捏肩膀揉揉胳膊,莫青荷全身腾腾得冒热气,抓起一条白毛巾胡乱擦汗,仍是止不住满身呱嗒呱嗒乱淌的汗珠子,干脆三下两下脱了上衣,往肩上一搭,光着胸膛吹风,水汪汪的皮肤印着昨夜的吻痕,他毫不在意,大喇喇地搂着沈培楠的肩膀:“走,走,这里让柳初盯着,咱们出去吸支烟。”
沈培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,他自己也奇怪,原本是众花丛中走、片叶不沾身的情场浪子,怎么就栽在了莫青荷手里,栽得心甘情愿、感情连绵不绝。他抚摸着无名指上的精光四射的钻石戒指,望着正在交接工作的师兄弟,感到没来由的醋意,莫柳初却对那道凶恶的目光丝毫没有察觉,他的注意力全在前来探班的王美云身上。
“沈哥,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待在这里吗?”莫青荷一脚踩着大厅门口的砖石花坛,挽起裤脚,露出一截修长紧实的小腿肚,他手里夹着一支烟卷,目光放得很远,“这里没有战争,没有党派,到处是最纯真的孩子,最纯净的知识和最纯粹的艺术,一切都是新的。”
“我多希望此时、在我们的家乡,也有这样一个崭新的中国。”
沈培楠破天荒的没有与他因为立场的问题展开争论,只是深深的吸了口烟,道:“有,一定会有,到了那时候,我带你回家。”
莫青荷远眺着秋日苍蓝的天空,视线跟随游移的白云,长长的发了一会呆。
大厅传来熟悉的胡琴声,悠远而苍凉,挑到最高又倏然收紧,于万籁俱寂处合上了儿童清亮的戏腔,莫青荷听了一会,笑道:“对了,沈哥,你不是爱听别姬吗,这一出我唱得实在不像话,但我找到一位再好不过的演员,你跟我来。”
沈培楠尾随他进去,那清脆的嗓音却忽然停下了,换成了另一名少年软糯柔和的说话声。
是阿忆。
练功房非常宽敞,阳光充足,三面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都镶嵌了巨大的金色穿衣镜,靠窗摆着几张实木化妆台,一名七八岁年纪的男孩坐在高背椅子上对着镜子勾脸,他还太小,两条腿从椅子边垂下来,脚尖够不到地面。阿忆站在一旁看他,大约是刚做完学校的功课,没来得及换衣服,依旧穿着私立学校的黑白色制服,踩着一双清洁的英式小皮鞋,脚腕翻出雪白的袜子边。
男孩举着毛笔,紧张的不敢下手,脸上匀着红红白白的半面妆,阿忆抢过笔,很有一位师哥的派头,一手抬起男孩的下巴,一手执笔,沿着他的眉弓勾出一道细致的黛眉,斜飞进漆黑的鬓发里去,他一边勾线,一边柔声讲戏:“刚才那几句唱的不好,虞姬别了霸王,除了悲,更有一个义字,一味悲悲切切,失了妃子的体面……”
沈培楠听得惊讶极了,阿忆只九岁,对这一折子戏的领悟不输成年人。
莫青荷露出得意的笑,回头望着沈培楠:“我想安排他正式登台。”
(三)
就在同一年的冬天,大洋彼岸两党派之间那场持续数年、声势浩大战争已经进入收尾阶段,堪称军事史上以少胜多战役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——淮海战役,在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对峙,付出伤亡十三万战士的代价,终于宣告胜利。那是多么辉煌的一年,在后来的很多年里,每每有人提起那一年的战况,依旧禁不住心潮澎湃……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乃至在温柔水乡里缱绻千年的江浙一带都招展起猎猎红旗,多么动人的消息,多么磅礴的胜利!
那段时间莫青荷常常做梦,梦里有爽晴高远的天空、飘扬着革命歌声的延河、穿灰布军装、打着绑腿的战友和兄弟,炮火轰鸣的战壕和山坳,战士们涌进各座城市,疲惫的眼睛里闪着希望,被尘土覆盖的脸颊盛开着最灿烂的笑容,满街的鲜花、红旗、雀跃的人群,耳边鼓噪着震天的掌声。
隔着宽广的太平洋往回看,有种隔岸观火的洞明,所有人都知道,战争就要结束了。
他在深夜猛然惊醒,眼角有温热的水渍,沈培楠也睡不沉,莫青荷翻身,他也跟着坐起来,两人在深夜里互相凝视,相对无言,忽然又像被火钳烫了,疯了似的扭打起来,追逐对方滚烫的嘴唇,在洒满月光的窗边紧紧拥抱。
沈培楠哑着嗓子叫一声小莫,说出口的话没了下文,莫青荷搂着他,一双手在他后背捶着打着,呜咽着喊沈哥,同样再说不出话。
那一段时间,他们几乎天天沉浸在这种要命的痴缠里,真的是要命,两个人发狠似的打,打到一半,气喘吁吁的往床上滚,每天早上爬起来都筋骨酸痛,一身的伤,一身斑驳的吻痕。他俩也怪不好意思,折腾一整晚,清晨洗漱时羞于相见,交流全靠佣人传话,倒像是在经历初次恋爱。
- 共178页:
- 上一页
- 第175页
- 下一页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- 11
- 12
- 13
- 14
- 15
- 16
- 17
- 18
- 19
- 20
- 21
- 22
- 23
- 24
- 25
- 26
- 27
- 28
- 29
- 30
- 31
- 32
- 33
- 34
- 35
- 36
- 37
- 38
- 39
- 40
- 41
- 42
- 43
- 44
- 45
- 46
- 47
- 48
- 49
- 50
- 51
- 52
- 53
- 54
- 55
- 56
- 57
- 58
- 59
- 60
- 61
- 62
- 63
- 64
- 65
- 66
- 67
- 68
- 69
- 70
- 71
- 72
- 73
- 74
- 75
- 76
- 77
- 78
- 79
- 80
- 81
- 82
- 83
- 84
- 85
- 86
- 87
- 88
- 89
- 90
- 91
- 92
- 93
- 94
- 95
- 96
- 97
- 98
- 99
- 100
- 101
- 102
- 103
- 104
- 105
- 106
- 107
- 108
- 109
- 110
- 111
- 112
- 113
- 114
- 115
- 116
- 117
- 118
- 119
- 120
- 121
- 122
- 123
- 124
- 125
- 126
- 127
- 128
- 129
- 130
- 131
- 132
- 133
- 134
- 135
- 136
- 137
- 138
- 139
- 140
- 141
- 142
- 143
- 144
- 145
- 146
- 147
- 148
- 149
- 150
- 151
- 152
- 153
- 154
- 155
- 156
- 157
- 158
- 159
- 160
- 161
- 162
- 163
- 164
- 165
- 166
- 167
- 168
- 169
- 170
- 171
- 172
- 173
- 174
- 175
- 176
- 177
- 178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