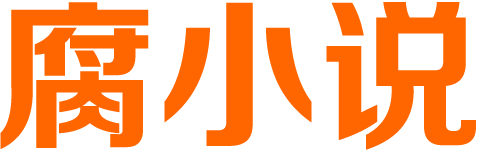一个无情的剑客(65)
我:“……”
为人处事还是要讲些道理,我真不是刻意坏你好事的。
江渊朝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,摹着纨绔子弟的口吻回应道:“我来明月楼是为着喝酒的,可不是成心听你的活春宫。”
隔着一层楼板,那人猛一拍桌,霎时间另一枚银铃嵌入砖石,周遭砖块应声裂开,竟是要将上下两间厢房打通。
此人丝毫不留情面,在窟窿能容纳一人通过时纵身向上一跃。
江渊眉目一动,电光石火间掐住我的腰往榻上一带,神情略带歉意:“别说话。”
江渊抚着后脑将我按进怀中,懒洋洋扭过脸去:“阁下好排场,我并非故意扰你好事,如今也算扯平了,何故还要刀剑相向?”
我不敢轻举妄动,只得按兵不动,听从他的指挥。江渊体量高大,将我遮得严严实实,我向外瞥去,只瞧见了一抹艳红的衣角。
“切莫生事!”一直未曾出声的第四人冷不丁开口。
也是男的?
我人傻了。
“郎君好颜色。”来人竟依言放柔了语调,望着江渊吃吃笑道:“不知郎君姓甚名谁,怎么称呼?”
江渊忽地扳起我的下巴,食指横于唇间,在指尖轻轻落下一吻,而后道:“鄙人从不做吃碗望锅之事,公子还是请回罢。”
“……好,奴家小字阿宁,近日都会在这明月楼停留,郎君若是何时放下了手中小碗,便来听奴家弹一曲琵琶罢。”
红衫、铃铛、琵琶……
他是先前那个怀抱琵琶的男子!
83.
楼下厢房空空荡荡,那两人言毕便另寻他处,徒留我僵滞在原地。
“宝儿?方才委屈你了,你没生江大哥的气罢?”江渊一瞬不瞬地望着我,我却迟钝地琢磨出了些事儿。
那自称阿宁的男人应是断袖,那他适才的意思是……
看上江大哥了?
“……小初?”江渊见我一时半刻没搭话,拧眉惊疑道:“怎么了,莫不是头痛又发作了?”
我连忙道:“不是不是!我晓得轻重的,怎会生气。”
我还是有些恍惚,江渊当我讳疾忌医,不由分说直接将刚坐直的我又按进了怀里,细长的食指轻轻按压两侧穴位,温声道:“方才那人在江湖中小有名气,我在外曾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迹,做事阴狠决绝,还是不与他起争执的好。”
是了,一枚铃铛直直**坚硬地砖,不说别的,这般内力必然是在我之上。
“还有一件事,”厢房寂静下来,江渊指尖顿了顿,“另一个人,似乎是你那林师兄。”
我倏然睁开眼,猛地从他膝上起身,仰起脸来,唇畔忽地一热。
我操。
素日里爹娘管得紧,这般粗俗之语决不会从我口中溢出。
可情势迫人,再找不到比这俩字更贴切我此刻心境的了。
“对不起江大哥!我、我不是有意……有意轻薄你的……”
他娘的,世上怎会有如此巧合,我起身时江渊刚好低头,两厢之下,我就这么突兀地擦过江渊的侧脸。
第64章 团圆(二)
84.
场面尴尬至极,惊诧之余上下牙一搭,我反倒咬破了自己的下唇,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。
哦,不需要我挖。
地上原就有个大洞。
洞已经准备好了,常雪初,你跳还是不跳呢?
85.
我最终还是没跳成。
江渊为人大度,扶额笑了起来,声音含笑:“小傻子,怎地这般纯情,今后娶媳妇时可怎么办呐?”
娶媳妇?
我缩了缩肩膀,这事不急。
除了时常外出的江渊,翠逢山上下无人不知,常小师弟正当年华,却随了几个师兄,没个结亲成家的意愿。
小半年前我一过十六岁生辰,冰人的目标便又多了一个。自溪里城来了个爽朗大方的冰人,将画像塞了我和谢陵一人一张,谢陵沉着脸夺过我手里的画卷,二话不说和他那张一同交还给人家。
我说:“陵哥,当面拒绝,恐怕不大好罢。”
谢陵横眉倒竖:“阿雪,你才多大,这些人就将主意打到你身上来了!”
我实在不好意思说,其实人家多半是冲你来的,我就是那个顺带的。
我也想不到哪家姑娘会中意我,毕竟在江湖上我的形象还是那个一等一的废物。
我默了会,道:“其实寻常人家十六结亲也是常事,但……”
“不可!”谢陵火急火燎打断了我未说出口的下文,艰难道:“……就是不行。”
我:“?”
没过几日,我又收到了第二幅画像。
谢陵吸取教训,说不上痛改前非,但好说没拦着,人却是不容拒绝地守在一旁,盯着我摊开画卷。
我看了一眼,揉揉眼睛,再看一眼,茫然道:“师兄,你看这画的是翠逢山吗?唉,里面那个人是我?”
谢陵不言不语,抬手卷走画卷,淡淡道:“或许是弄错了吧。”
我原本想说那画卷底下似乎有字……算了。
两月后,清泉派文掌门携同座下弟子前来与剑宗弟子切磋。
文掌门有个和我一般大的儿子,名唤文心远。文心远是为数不多待见我的同辈之一,逢年过节各派往来之际,他常在信中问候我一两句,算是我在剑宗外的一个朋友。
“常师弟,”文心远鬼鬼祟祟凑到我边上,红着脸拉住我的手腕,“前些日子我托人送了幅画给你,你可有收到?”
我:“?”
你这个人没事红什么脸?
我想了一下,一拍脑袋记起那幅来历不明的画卷,恍然大悟:“原来是你的画啊,画得挺好看的。”
文心远眼睛一亮,继续道:“那画底下的小字,你可瞧见了?”
我:“?”
这个真没有,我还没瞧见就给谢陵抽走了,当然我也不好告诉他实情,只得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。
文心远那张小白脸愈发的红,看着像是做了甚么坏事被人揭穿了一般,期期艾艾道:“常师弟……那你是怎么想的?”
我:“?”
没法糊弄了,我说:“什么怎么想的?”
文心远急了,抿了半天下唇,一个字也没从嘴里蹦出来。
刚巧我爹唤我,我便不打算同他在这儿继续打哑谜,一溜烟跑走了。
原来我爹找我也没好事。
持剑上场前我在继续当一个废物和小露一手之间摇摆不定,清泉派弟子已拔剑而来,秉持着不给剑宗丢面儿的原则,我终是接了他的招。
那结果自然是侥幸未辱没剑宗门楣。
嗐,在几个高手轮番高强度教学之下,任谁都不会没一点长进。
我爹呷了口茶,慢悠悠道:“雪初,你与文贤侄一向要好,不若趁此良机切磋一番?”
没必要罢!
文心远能力排众议同我做朋友,我一直以为缘由是我俩的功夫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,一个赛一个的不争气。
我试着婉拒,架不住文心远摆出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。
……是真的没必要。
文心远手中剑坠地,震惊与伤心揉作一团挂在脸上。
唉,文小兄弟,打赢你这种事情,我也不想的。
不想文心远这厮的小情绪一时难以消解,大半夜的站在门外一声一声地喊常师弟,跟叫魂儿似的。
不是我不愿请他进来一坐。
而是谢陵这浑人又捂着心口声称自己做了噩梦,半个时辰前刚偷摸爬到我床上。
旁人看见总不会认为是谢陵铁了心非要与我同榻,必定是腹诽我胆子比针眼小,这么个十六七的人睡觉还要拉着师兄作陪。
我说:“文师兄,我歇下了,有甚么事明日再说罢。”
文心远伫立门外,静了一会儿乍然开口:“……常师弟,想来白日里你是唬我,甭管你收没收到那幅画,将窗台上的信收下吧。”
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!